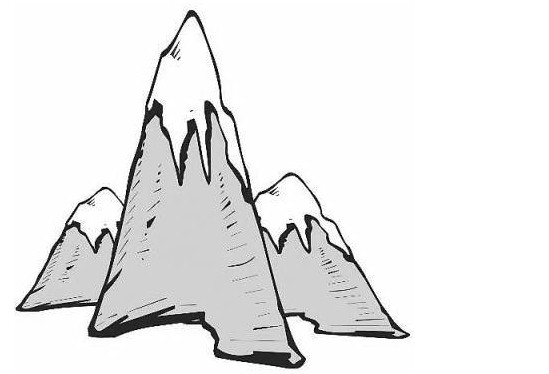
“钱学森之问”,既是一个“科学之问”、“教育之问”,实际上,更是一个“体制之问”、“历史之问”。它的科学求解,确实关乎国家未来长远的兴衰发展。
科学与自由,科学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分割”,恰是“钱问”产生的生发之源,“融合”也恰是“钱问”最终求解之宗、之路。
一篇不旧的“旧作”
“钱学森之问”近些年震动朝野:为何几十年来中国出不了大师、大家级的科学、文化人物?人们纷纷求解作答。这不由地让我回忆起一段往事。1988年年末到1989年三四月间,我曾被邀介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发展与改革问题”决议草案的讨论。事情缘起于我当时实际主持、主编的《科技导报》,在1988年第5期上刊出了《导报》分别在美国、北京举办的两次关于中国教育问题的专家、校长座谈会发言纪要,以及我专门为此写的一篇刊首评论员文章《一个极待重新审度的大计——关于教育问题的思考》。这期《导报》国家教委要去了60本。时值中共中央四中全会上要就我国教育改革问题作出正式决议,正在筹备决议文本的起草工作,由当时的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和中办主任温家宝牵头。由于《导报》对上述教育问题的适时探讨、报道和评论,引起上方领导的重视,我也被额外邀请去玉泉山参加了文件起草顾问组的几次讨论、修改工作。
也恰是在头两次讨论中,我系统论述了对我国教育指导思想的几个重要反思。论述了由于几十年来在教育、育人上违背少年儿童情感、思想、观念成长的客观规律,用概念化、抽象化的政治思想教育,替代由真善美、假恶丑具象对比引导的做人、为人的品德启蒙教育,导致政治思想教育失误失效,未能在一代代青少年中树立起真正自觉,发自内心悟性的思想、信念和理想、理念;更在改革开放,打开国门,面向世界的新形势下,出现普遍的信仰危机。同时,我也着重分析、论述了由于长期倡导在各方面、各领域中求同斥异的大一统教育,在种种排斥“求异”、“存异”、“容异”思维教育思想的引导下,一代代人在思想、性格、个性、思维上普遍趋同化、雷同化的现象。分析、预警了这些现象、趋势,必将导致社会成员逐渐失去创造性、发展性、突破性思维这一人类最大潜在优势的严重后果。
由于我对青年一代抱有特殊的期待,故为《中国青年报》专门撰稿,发表《反思教育思想对民族素质的深刻影响》一文,比较集中地表述了我在玉泉山里的发言要点和论证概要。
不想,此篇20多年前旧作中的种种忧虑、思虑,种种可称之为“马前炮”的预警、预告,如今再对照当前种种现实来看,不仅不幸言中,而且是大大地言中了。一些资深的专家、学者,认为我这篇旧作,仍不失为对当下“钱学森之问”索源探由的一种探讨思路,认为在未来“亡羊补牢”中尚有意义和作用。
“钱问”是“体制之问”、“历史之问”
毋庸置疑,“钱学森之问”,既是一个“科学之问”、“教育之问”,实际上,更是一个“体制之问”、“历史之问”。它的科学求解,确实关乎国家未来长远的兴衰发展。无怪乎2007年钱老在病榻上向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提出此问后,顿时间,惊动上下,震动朝野。温总理很快先后两次委托复旦大学前校长、时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的杨福家院士邀集有关专家学者专题研讨。第一次在中南海,温总理亲自与会聆听。第二次是2008年年初在广州中山大学,历时两天,有20人左右,多为离退休学界学者。这次我也有幸被邀,忝列参加。会议结束时,杨福家教授郑重表示,将认真整理大家意见,如实向温总理汇报转达。当时总理和中央对“钱老之问”之重视,之下力探索,由此可见一斑。
为何说“钱学森之问”更是“体制之问”、“历史之问”?在我看来,它深深涉及我们10多亿人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实践,涉及对社会发展的历史探索和历史经验的回顾和反思。若再放开眼界,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也涉及对20世纪全人类科学文明、人文文化上的历史大实践、大探索的回顾、对比与反思。这确实是一个在历史当口上,对国家民族高度负责的严肃之问、睿智之问。
不言而喻,“钱学森之问”既然是严肃的“科学之问”,那么它真正的求解,必然离不开“科学”,即离不开“科学理性”、“科学精神”。既然也是一个重大严肃的“历史之问”,那么它最后的求解,也必然离不开“民主与自由”,即离不开当代人类文明的“人文文化”和“人文精神”。
求解“钱问”的关键要害
可以说,中外近现代发展史,已一再证明,没有真正的科学精神,也就难以孕育出真正的实质民主。反之亦然,什么样的民主发展程度、高度,也必然决定着、衬映出什么样的科学发展程度、高度。这也正是我们当下民智普遍不彰、民慧难以普遍涌现,也难出大师、名士的关键症结之所在。
何出此言?请读以下分析。
一、从李政道的名言,看“科学与人文”、“科学与自由”、“科学与民主”间的本质关联。
李政道有句名言:“科学与艺术是一个钱币的两面。”为什么李政道会从他的科学生涯中体会出这句名言,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我的理解是:一个人不论是在科学上,还是在艺术上(艺术属于人文,也可代称为广义的人文),真正能实现其执着的追求,能达至辉煌的高峰,最必需、最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恰恰是:自由的心灵,自由的意志,自由的思考,自由的探索和自由的表达。这五大自由,对任何一个人,要达至任何科学与艺术的高峰,都是缺一不可的。众所周知,自由是民主的佑护神,自由与民主也是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的。简而明之,没有真自由,就没有真民主,也就难有高科学,难有高艺术。从一定意义上讲,科学艺术发展的程度高度,也是检测自由民主发展程度高度的晴雨表、测试剂。而且在我看来,民主与科学的长期被分割,长期被脱节,也恰是“钱问”产生的主要根源、症结之所在。
二、从科学精神、科学理性所内涵的六大实质要素,看科学与民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不可分割。
我学理工科出身,一生的工作也在科学活动大范畴内,当然熟知自然科学发展、演进到今天这样一个坚实、可靠,既相贯通、又相佐证的知识体系和认识体系,其必有一个精髓、一个主轴贯穿始终,方会演绎出如此严谨的逻辑,如此贯通的结构,如此精确的结果。这个主轴、这个精髓就是科学精神和科学理性。
但我又一再困惑,多年来“科学精神”、“科学发展”的口号天天、处处喊得震天响,可是浮华、浮躁,种种假、大、空的套话,种种剽窃造假诈骗的恶行恶状又经常招摇过市,恶性膨胀,成了难以抑制的社会癌症。
痛定思痛,我想,关键在于一定要把“科学精神”、“科学理性”中可实践可检验的实质要素明确、简洁地梳理出来,使之成为人人可理解、可掌握、可实践、可对照检验的思想利器,让一切“假借科学之名的伪作者”无处藏身,无路可遁。谁是在空喊口号,谁是在认真践行科学精神,推动科学理性,往往可以一目了然。
我是从科学的本征出发,来逐步思索归纳梳理这些要素的。
什么是“科学的本征”?我认为可以归结为两点:1.科学是人类每一世代,每一个人,以自身有限的主观认识能力,去认识外在无限客观存在的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2.在这个过程中,又总是后人发现前人认识上的不足、偏差,补充纠正前人的认识错误,修正推翻前人的错误结论而前进,而越加接近客观真实的。
正是在上述两大科学本征的基础上,我进一步做了思考、梳理,认为科学精神、科学理性至少应该包涵以下六大实质要素,即:“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宽容的激励。”我认为,这六大要素,是任何一位科学家在他一生的科学活动、科学探索中须叟不可离,缺一不可为,少一难为继的。实际上,人类历史上一切新发现新发明,以及一切发展性、创造性、突破性新思维的产生,也无不是经过这六大要素的反复证实、证伪的结果。
试想想,如果这六大要素,最终成为我国广大公众、公民有法律保障的一种思想权利,成为人人手中判识一切事、一切人其背后真伪的思想利器——也就是人人皆可依据客观存在和客观实际,来理性分析,理性判断;进而能有依据地提出理性怀疑和理性问质,还能由此再自由、自主地,不受限制地展开寻求解答的多元思考,又能在各种多元思考、多种不同意见的讨论、争论中懂得尊重各方的思想权利、争论权利,并从中吸取正确、有益的成分;又能在平权争论后自觉地共同接受实践(包括实验)检验的结果;最后还能大度宽容各种探讨、试错过程中的失误、失败——那么,一个处处充满了自由、民主、理性、宽容的社会大环境不就油然而现了吗?在这样的社会环境、氛围中,我们社会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民智民慧,不也就必然会大量涌现,勃然而发了吗?
试想想,前30多年,我们不正是因为开放了市场经济,才使得广大的公民、公众人人皆得以有权利、有机会通过市场的公平竞争(尽管当下,在种种权钱交易下,市场环境尚很不透明,很不公平),来展现自己的能力,依靠自己的艰苦劳动、奋力拼搏,为自己、为家庭创造积累自身切实拥有的财富,争取自己人生发展一步步成功。
特别是,亿万中国农民和农民工,得以摆脱几十年间的土地禁锢、农村禁锢,获得人身和劳动的初步解放,他们在争取自身人身解放、经济解放和勤劳富家的奋斗中,也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大业,作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贡献。这场30多年的经济改革、民生解放,确实大大释放了民间压抑、蕴藏了几十年欲求自主、自立、自发、自由地去创造自身财富的无穷动力和活力。这种亿万人动力、活力的大解放、大释放,才是最终促成中国现代化史上这一场震惊世界的经济大发展的根本原因。
循此,再试想想,倘若我们也能像经济改革、民生解放那样,真正有步骤地推动一场伟大的政治改革、民主解放,那么,我们蕴藏了几千年的人文文化,民智民慧,当然也包括科学技术领域的种种潜能潜力,不也必然会引发出普遍的涌现和澎湃勃发吗?我曾多次在讲座交流中把美国包揽大多数诺贝尔奖,比喻成一座充满创造创新活力的大冰山顶尖上不断闪耀出的光芒。如果我们国家、民族这座大冰山的底层和主体,通过政治改革和民主解放,也能像市场经济带来巨大动力、活力那样,在精神、思想、科学、文化领域获得民智民慧的大解放、大释放、大勃发,又何愁在我们大冰山的顶尖上不会连连向世人闪耀出傲人的光芒?“钱学森之问”不也就豁然而解了吗?
总而言之,我以为,以“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宽容的激励”为内核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互为表里、融通一体、不可分割的。同理,科学与自由,科学与民主也是不可分割的。“分割”,恰是“钱问”产生的生发之源,“融合”也恰是“钱问”最终求解之宗、之路。
无独有偶,在一次专题研讨“钱学森之问”的小型学术会上,3位并列而坐的老学者,各用了一个关键词,来表达自己对“钱问”出路的见解。84岁的北京大学资深教授陈耀松说“要靠民主”;紧接着,88岁的力学家郑哲敏院士说“要有自由”。(之后不久,即2013年1月,他获得了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接着,95岁的中国科技大学备享盛名的李佩教授说“要能争论”。此情此景,真是美妙极了,我当时心灵一震,永世难忘。3位白发苍苍,却言简意赅,“科学与民主”、“科学与自由”、“科学与争论”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可见神州大地上的仁人志士、各方学者,大势之观察,可谓不约而同;症结之判断,亦所见略同。
行文至此,不论朝野,不分上下,借问读者诸君,本文上面的所述种种,合理吗?正确吗?当然,亦可存疑,亦应多元再思考。有疑有思,就有所悟,就有进步;有疑有思,就有变化,就有希望!切不可对上述诸述诸问,视而不见,避而不就。要知道,振兴中华,贡献人类,上下朝野,人人有责,尤其肩负大责大任者!
文字作者:蔡德诚 摘自《 中国青年报 》
文章来源:http://zqb.cyol.com/html/2014-05/02/nw.D110000zgqnb_20140502_1-03.htm;